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
死亡是生命形态的转换
死亡是生命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应当如春华秋实般被理解和接纳。然而,现代医学手段在延长生命的同时,往往带来了对生命终局的扭曲认知。过度治疗可能让患者在临终时承受不必要的痛苦,甚至成为对生命的“软暴力”。
因此,安宁疗护所倡导的“自然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终”理念一脉相承,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和患者意愿的基础上,让生命以尊严谢幕。尊重患者在清醒时表达的生命嘱托,既能帮助其实现圆满,也能减轻家属的道德压力。
对于丧亲者而言,哀伤不是疾病,而是爱的延续。现代哀伤辅导专业不再简单要求人们“放下”或“走出来”,而是鼓励为哀伤找到出口。在实践中通过“双程模型”,既允许生者的情感自然流动,也帮助其重建生命意义。
无论是记忆盒、生命故事书,还是以遗物制成纪念物,这些“持续联结”的方式都能为哀伤提供疗愈的可能。尤其是失独父母等特殊群体,更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同路人的陪伴,在“与悲伤共生”中逐渐获得力量。
死亡不是终结,而是生命形态的转换。现代哀伤辅导的终极目标在于帮助生者重建意义世界,通过遗物整理、未尽事宜完成等仪式,得以延续其生命价值,重新锚定生命坐标。
因此,面对亲人的离世,需要建立起涵盖医学支持、心理重建和社会关怀的立体化应对体系。通过预立医疗计划、安宁疗护、专业的哀伤辅导和社会支持网络,可以实现从生命终末到哀伤陪伴的全周期关怀。这不仅是对个体的疗愈,更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北京协和医院国际医疗部主任助理戴晓艳:
缓和医疗是人文的,更是专业的
缓和医疗发展的核心在于专业性,而不仅仅是社会普遍认知中的“爱心、耐心”或“人文关怀”。
以癌症为例,肿瘤科医生的重点在于关注病情发展与治疗方案,而缓和医疗团队会聚焦于患者作为生病的“人”在身体、心理、精神、社会层面的痛苦,与肿瘤科携手给予患者及家人更完整的全人照顾。在症状控制方面,缓和医疗提供更为精细的管理;在死亡准备方面,缓和医疗通过开放而专业的沟通,帮助患者和家属逐步面对现实,而不是像临床中常见的那样,仅停留在告知患者家属“需要签字”的层面。
缓和医疗团队同时也会循序渐进地了解患者的真实想法、家属的心理准备以及他们对死亡的认知程度,并在这一切逐步铺开并得到回应时,真正发挥价值。
所以,缓和医疗的发展依赖于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目前国内专业医生依然稀缺,尤其是能够系统掌握症状控制、心理支持与沟通技巧的专科医生更为有限,这一人才短板也是推动学科进步必须面对的现实。
同时,缓和医疗并不是在患者去世的瞬间画上句号,团队还需要继续陪伴家属,帮助他们度过哀伤期。
在整个照料过程中,有效沟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倾听。倾听不是沉默,而是带着同理心去感受并追随患者与家属情绪的流动,有时一个眼神、一句简短的回应都能传递力量,而这本身已构成治疗的一部分,也需要专业的培训。
许多患者或家属在门诊中通过哭泣宣泄后,常常会在离开时表达“太好了,谢谢你”,这正说明倾听与陪伴本身已经构成了治疗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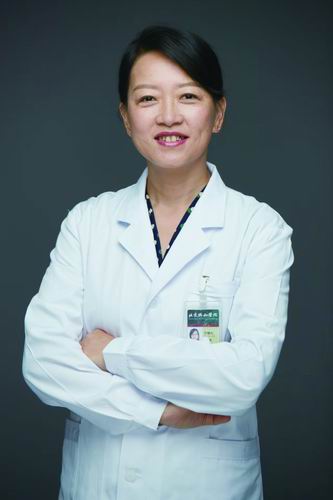
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主任宁晓红:
缓和医疗在中国“生根发芽”
缓和医疗是现代医学的回归与圆满。它以缓解症状为核心,旨在改善患者、家属及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将医疗技术与人文关怀相结合。
缓和医疗不仅帮助患者管理身体痛苦和心理焦虑,也支持家属的情感调适,使重病患者在病程中尤其是生命末段得以平静、有尊严地度过。它贯穿疾病全程,与抗癌治疗等各种原发疾病的治疗并行,而非仅仅针对临终阶段,是对生命完整性的尊重,也是对现代医学过度聚焦延长寿命而忽视痛苦减轻的补偿。
在医疗体系中,缓和医疗弥补了此前在临终关怀上的缺失,使死亡能够被专业、从容、温暖地对待。缓和医疗不仅是医学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满足患者与家属全方位需求的重要途径。它通过全人照护模式,使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同时也消除了“缓和医疗等于放弃治疗”的误解。
在我国,缓和医疗仍处于发展阶段。尽管部分城市和医院已开展实践探索,但整体普及率低,教育培训体系尚不完善。
目前,我国缓和医疗教育体系化建设亟须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其一,应在医学院校合适年级开设缓和医疗的必修或选修课程,帮助医护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并提升他们应对死亡的能力;其二,应建立成体系的继续教育计划,使在岗医护人员能够通过学习相关知识,减轻在终末期照护中可能产生的“无力感”;其三,应根据临床岗位设立胜任力目标,通过分层次的培训和资质认证保障医护人员具有缓和医疗能力。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安宁疗护一体化的健康和养老服务,促进慢性病全程防治管理服务同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紧密结合。”
随着国家政策引导、医疗机构探索以及教育培训的不断推进,缓和医疗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人口老龄化、社会对生命质量的关注以及政策支持为其规范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基础。同时,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在症状评估和信息提供等方面能够辅助医疗,但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希望更多年轻医护进入这一领域,将缓和医疗推广至更广泛的人群,让爱与关怀伴随人生的所有时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干细胞移植科主任医师周翾:
让有限时间充满尊重与爱
儿童安宁疗护的核心在于“全方位关怀”,不仅关注患儿的生理痛苦,更重视其心理状态及家庭的情感需求。孩子不仅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未来。当医学无法逆转疾病时,安宁疗护的目标是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感受到无限的爱与尊重。
15年前,我们团队曾经救治了一位5岁白血病患儿。患儿病情严重、持续复发,长期咳嗽且痛苦难眠。我们尝试各种办法缓解患儿出现的症状,但依然收效甚微。最终,患儿母亲选择放弃终末治疗。
患儿平静离世,母亲为她化了淡妆,好像她仍活在世上。
这段经历是我理解儿童安宁疗护的起点,也深刻体现了安宁疗护的核心理念: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爱与陪伴。
自2013年起,我开始投身儿童安宁疗护工作。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个体化陪护,尽量在下班及休息时间陪伴孩子和家属。
2017年,在我的倡导牵头下,我国首个家庭式儿童安宁疗护病房——雏菊之家在北京启用。我们推行“居家+机构”联动模式,由医生、护士、社工、心理师共同参与,提供全程照护。
儿童安宁疗护不是冰冷的医疗行为,而是一场以家庭为中心、尊重孩子的温暖旅程。
我国儿童安宁疗护起步晚,需求迫切。目前全国儿科医疗机构安宁疗护床位不足50张,许多家庭在重症监护室与家之间挣扎,缺乏专业舒缓治疗支持。儿童的疾病谱、心理状态和情感需求与成人不同,因此需要更细腻的照护模式和更专业的跨学科团队。
儿童安宁疗护是一种权利,医疗与人文关怀应向所有孩子平等覆盖。
在技术和创新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辅助疾病评估、科普和医学建议,而远程医疗能够为偏远地区家庭提供专业指导,提升治疗效果。不过,技术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儿童安宁疗护领域仍需要更多具备医学技术与人文情怀的医生参与。
我们应从儿童时期开始,帮助公众理解死亡不是终点,安宁疗护不是放弃。青年医生应该勇于加入这一领域,具备勇气与慈悲,在陪伴孩子、倾听梦想的过程中找到坚持下去的力量。
通过全周期关怀、家庭中心模式、MDT以及心理和情感支持,儿童安宁疗护不仅缓解了患儿的痛苦,也让家属获得力量与支持。每一次努力,都让离别的哭声少一些,让微笑和温暖多一些。这不仅是对患儿和家庭的关怀,更体现了医学的人文本质和温度。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
从“延长生命”到“呵护生命”
中国安宁疗护的发展是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助于节约医疗支出,提高医疗资源效率。
随着我国癌症发病率持续攀升,晚期癌症患者对减轻痛苦、维护尊严的医疗需求日益迫切,而常规放化疗在晚期患者中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对身体状态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发展安宁疗护成为临终关怀和缓和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世纪80年代安宁疗护被引入我国,尤其是自2017年开展全国试点工作以来,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各地通过政策引导和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整合式安宁疗护路径。
例如,上海构建了“医院-社区-家庭”三级网络,北京协和医院开展了“叙事医学培训”,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探索了“安宁疗护服务模式”等。这些实践表明,人文医学理念与多学科协作的融合能够显著提升晚期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家庭照护满意度,使患者能够有尊严地完成生命的“最后一公里”。
临床数据显示,晚期癌症患者疼痛发生率高,且随着病理分期加重,疼痛程度加大。然而,约三分之一的患者癌痛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安宁疗护床位和服务覆盖仍远低于实际需求。
《2025—2030年中国安宁疗护机构行业投资价值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需要安宁疗护,但现有床位不足20万张。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安宁疗护服务在三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覆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在实践探索方面,上海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建立三级网络、优化疼痛管理流程、增加专业培训,显著提升了基层安宁疗护的效果。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于2017年3月6日正式挂牌成立了安宁疗护中心,这是国内第一家拥有独立病区的三级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北京协和医院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综合服务,包括症状管理、心理支持与灵性关怀,并开展沟通技能培训以提升医务人员能力。由此可见,多学科协作和标准化流程建设是提升安宁疗护质量的核心要素。
在制度建设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自2019年开展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以来,全国设有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科的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增加,截至2022年已达4259个。
尽管取得进展,我国安宁疗护仍面临结构性挑战。按国家规划,到2025年每个试点市(区)和每个县至少设立1个安宁疗护病区,但当前服务仍无法满足需求,发展仍存瓶颈。
为此,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完善服务标准,参照WHO指南制定本土化控制路径;强化社区能力,推广基层实践经验;改革支付制度,扩大终末期医疗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并建立考核激励机制;推进死亡教育,将生命教育纳入全民健康教育体系,降低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偏差。
中国安宁疗护体系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关键阶段。实践表明,通过多学科协作、社区网络建设和支付制度创新,可以有效提升终末期患者的生存质量。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循证研究、完善政策框架,实现从“延长生命”到“呵护生命”的医疗价值转型。
《医学科学报》 (2025-09-26 第4版 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