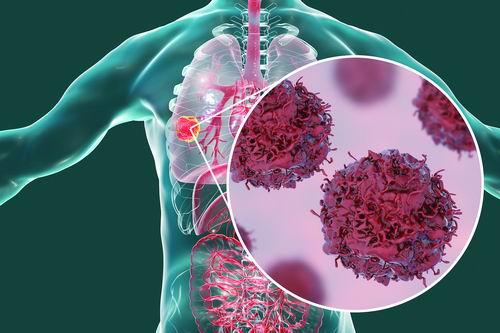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本报实习生 张芸萱
肺癌是世界各国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
数据统计显示,我国2022年肺癌新发病例106.06万,占全部恶性肿瘤病例的22.0%,死亡病例73.33万,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病例的28.5%。
通常早期肺癌多无明显症状,临床上多数患者出现症状就诊时已属中晚期。晚期肺癌患者整体5年生存率在20%左右。
为进一步规范中国肺癌的防治措施、提高肺癌的诊疗水平、改善患者的预后、为各级临床医务人员提供专业的循证医学建议,中华医学会制定了《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通讯作者之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教授王洁表示,相较于2024版指南,2025版的更新内容包括,在筛查部分新增了不推荐参加肺癌筛查的人群,强调了对肺癌高危人群开展低剂量螺旋CT(LDCT)检查前,应充分告知筛查的可能获益与潜在风险。
肺癌筛查的起始年龄为45岁
早期筛查是肺癌防治的关键环节,对于降低肺癌死亡率和提高患者生存率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肿瘤统计数据显示,肺癌的年龄别发病率及死亡率在45岁之后显著增加,因此《指南》推荐肺癌筛查的起始年龄为45岁。
在肺癌高危人群方面,《指南》结合中国人群肺癌的发病特点,推荐在符合年龄段的基础上,对含有下列危险因素之一的人群进行肺癌筛查。
首先是吸烟人群。吸烟是肺癌发病的首要危险因素,吸烟量与肺癌发病风险呈线性正相关。研究显示,吸烟量大于20 包年的人群患肺癌的风险显著增加,且即使在戒烟超过15年后风险仍高于从未吸烟者。
其次是二手烟或环境油烟暴露者。二手烟暴露可显著增加肺癌发生风险,炒、炸等烹饪方式产生的厨房油烟也可能导致 DNA 损伤或癌变,是中国非吸烟女性罹患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最后是职业致癌物质暴露者。长期接触氡、砷、铍、铬、镉及其化合物等高致癌物质者更易罹患肺癌,石棉暴露也可显著增加肺癌的发病风险。另外,二氧化硅和煤烟也是明确的肺癌致癌物。
此外,有个人肿瘤史、一二级亲属肺癌家族史、慢性肺部疾病史的人群都是肺癌高危人群。
在筛查手段方面,《指南》推荐采用LDCT进行肺癌筛查。多项研究显示,与胸部X线比较,LDCT可显著提高肺癌的检出率并降低肺癌相关死亡率,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不过,在对肺癌高危人群开展LDCT检查前,医疗机构应充分告知患者筛查的可能获益与潜在风险。
对于因自身因素,预期不能耐受以根治为目的的治疗(如手术、放疗、消融等)的人群,不推荐参加肺癌筛查。
诊断需要结合影像学和病理学
《指南》指出,肺癌患者的临床表现多样。中央型肺癌可表现出咳嗽、咳痰、咯血、喘鸣、气急、胸痛、声音嘶哑、吞咽困难、上腔静脉综合征、膈肌麻痹、胸腔和心包积液、肺尖肿瘤综合征等。远处转移可因转移部位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症状。
周围型肺癌早期常无呼吸道症状,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可出现相应的呼吸道症状或转移引起的相关症状。少数肺癌患者则会出现一些少见的副癌综合征,常表现为胸部以外的脏器相关症状,如高钙血症、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征、异位库欣综合征、神经肌肉功能异常、血液系统异常等。
在肺癌的诊疗流程中,诊断环节也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后续治疗方案的制定与患者预后。《指南》指出,肺癌的诊断主要有医学影像学检查、获取肺癌细胞学或组织学检查以及血清学实验室检查。医学影像学检查方法主要包括X线摄影、CT、磁共振成像、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超声、核素显像等方法。
影像学检查主要用于肺癌诊断、分期、疗效监测、再分期及预后评估等。《指南》建议根据不同的检查目的,合理、有效地选择1种或多种影像学检查方法。
获取病理学标本时,若条件允许,除细胞学取材,《指南》建议尽可能获取组织标本,除用于诊断,还可以进行基因检测。血清学检查则有助于肺癌的辅助诊断、疗效判断和随访监测。
临床还推荐常用的原发性肺癌标志物有癌胚抗原、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胃泌素释放肽前体、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等。
王洁表示,肺癌的诊断通常需要结合影像学和病理学检查。虽然肺癌血清肿瘤标志物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不高,但其升高有时可早于临床症状的出现。因此,检测肺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有助于辅助诊断和早期鉴别诊断并预测肺癌病理类型。
治疗手段更为多样
在明确肺癌诊断后,制定精准的治疗方案是提升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关键。《指南》依据肺癌的不同分期,提出了个性化的治疗原则与策略。
首先,对于早期肺癌(Ⅰ、Ⅱ 期)患者,根治性外科手术切除是首选治疗方法,解剖性肺叶切除是标准术式。对于部分特殊患者,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也可考虑亚肺叶切除术。对于部分高危患者,术后可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辅助化疗或辅助靶向治疗。
其次,对于局部晚期肺癌(Ⅲ 期)患者,要根据是否可以手术进行治疗。多学科综合治疗是关键,包括新辅助治疗、手术切除、术后辅助治疗等。新辅助治疗可选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等方案,术后根据病理分期及分子检测结果给予相应的辅助治疗。不可手术的患者则以立体定向放疗为首要治疗模式,除了需要考虑肿瘤因素,还需要结合患者一般情况和治疗前有无明显体质下降,以及正常组织器官对放疗的耐受剂量等进行综合考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放化疗剂量。
最后,对于晚期肺癌(Ⅳ 期)患者,免疫治疗成为重要力量。对于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阳性的非鳞状细胞癌及鳞状细胞癌患者,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激活其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细胞,为患者带来新的生存机会。
当然,传统化疗仍是晚期肺癌治疗的基础方案之一。对于不适合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的患者,《指南》推荐了多种化疗方案。例如,非鳞状细胞癌患者可采用培美曲塞联合铂类药物化疗,鳞状细胞癌患者则可选择紫杉醇联合铂类药物等方案。
此外,放疗在晚期肺癌治疗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出现局部症状或远处转移的患者,如上腔静脉综合征、脊髓压迫症、脑转移、骨转移、阻塞性肺不张等,放疗可以有效缓解症状,控制肿瘤进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王洁表示,随着治疗手段的丰富,早中期术后及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基因检测内容有了新的调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基因突变患者在单药治疗之外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多联合治疗的应用可以实现更好的疾病控制。
此外,免疫新辅助、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耐药后肺癌患者有了更多的治疗策略。而对于既往缺乏治疗手段的基因突变、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突变及耐药后的小细胞肺癌等,新药将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疗效。
《医学科学报》 (2025-08-15 第11版 指南)